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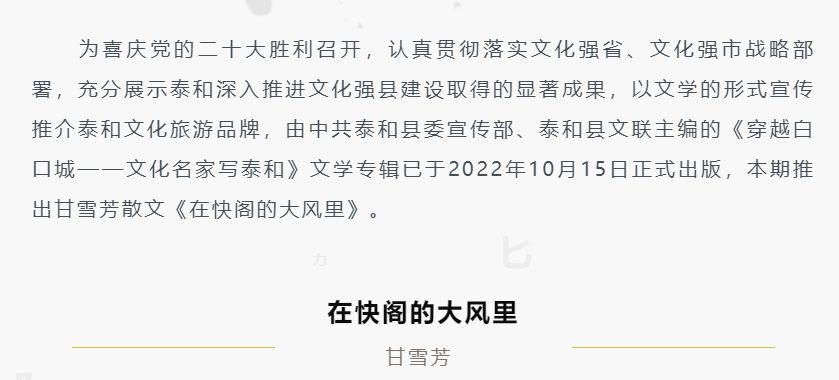
一
我们爬上阁楼顶层。连日酷热的七月,这一天的气温骤然降下来,阴凉而镇静,间或有大风吹来。
“前面便是曾经的澄江”,泰和文友肖城生指着近处一方被美人蕉簇拥的绿水告诉我,“快阁当时位于县城东门,澄江沿城墙流动,充当护城河。”
“山是紫瑶山,道教胜地”他的手指移向目之所及的最远处。似乎他就是曾经生活在近千年前的古人,站立的是近千年前那座阁楼,看见的是近千年前的风光,他的手指在空气中一重重地,来来回回地移动,像在指点一张新鲜地泛着墨香的北宋江山图。“楼前泛着银光的,是赣江”说到这儿时,他两手撑着廊台前的栏杆,陷入沉默。他今天穿的白衬衫,清爽平头,其间纷呈丝丝雪白,脸色里有岁月带不走的文艺气息。
“你知道吗?读书时我常来到这里,趴在栏杆上,看大江,听风声。”原来与阁楼毗邻的便是他的母校,泰和中学。想起八十年代的黄金岁月,他变得兴奋起来,谈起学校有一个心照不宣的传统,清晨或傍晚,总能在阁楼上听见学生们的琅琅书声,当然,也有像他这样的追风少年,一个人爬到楼顶,看赣江潮涌。江水从万安的十八滩奔来,歌谣中“十船过滩九船翻”的十八滩,一到泰和段,水域豁然宽广,云彩缱绻舒展,水天相接,满目澄明。
“真是开阔啊,看着小船一路顺流而下——”他依然停留在少年的心绪里,“真是天大地大”。
二
这是1082年的深秋,黄庭坚再次登上这座阁楼。楼不算特别,三层,高台回廊,飞檐如翼,和赣江上游的郁孤台、下游的滕王阁相比,既不算雄伟,也不算清幽。但于他,却是公务之余,可以将身心全然交付的所在。记不得有多少次来到这里,他暂时忘却世事纷扰,在江风的吹拂中让激越的心跳渐渐安顿下来。
从奔赴这个地方开始,至今快三年了。拜那次著名的历史事件所赐,当然也是他的自主选择。率性耿直,傲字是他身上的刺,让他这一生都难以避开。一路行舟,类似一次放逐。那时他并不期待尽快面对现实,即使这是他仕途上的第一次主政。一派繁荣下的北宋王朝,被旷日持久的党派之争急速消耗着元气,内忧外患,危机四伏;官场的深不可测,两任妻子的相继离世,敬重的师友多被贬谪,人世的无常对心脏反复鞭打,这个小小的县城能承载得下这份沧桑忧怀吗?
一路上,他拜亲会友、寻访古迹,不断调整心绪。“山谷道人”便是途经山谷寺时他为自己取的名号。“石盘之中有甘泉,青牛驾我山谷路”,此后,这个称谓便如苏轼的“东坡居士”一样,在人群中口口相传,走过了千年岁月。
他带着这个具有清逸山林气息的称号赶来,带着企图脱胎换骨的心愿,风尘仆仆,走马上任。从县尉到国子监教授到知县,从叶县到汴京再到泰和,十几年光阴匆匆流逝,道阻且长,好在如今为政一方,掌握实权,骨子里的济世情怀终于可以施展拳脚。泰和地处江西中南部,多山多丘陵,因“地产嘉禾,和气所生”而得名,赣江所到之处,飘溢着樟香、酒香、墨香以及明亮的市井烟火之香。乡愁的味道。
此后近3年的时间,在这里,他躬身经营着自己的首块试验田,也是在这里,他遇见了自己的第三任妻子。
三
刚上任时,正值春耕时节,他带着属官到县城附近巡视,却见广袤的田野冷冷清清,寥寥几个耕者不是年老便是体弱,询问缘由,才知是朝廷推行青苗法,以种田多寡确定税赋,农民苦不堪言,转而经商者、欠税逃役者、沦为盗贼者为数众多。
他写信给朋友诉苦:溜绳索偷盗的人才刚抓进监狱,持刀械斗的人又到了法庭,监狱人满为患。局面混乱,闻所未闻。在汴京做学官时,位于政治漩涡的外沿,尚可以做象牙塔里的清风客,但作为一县之长,是政府组织的神经末梢,必然与高涨的改革变法劈然照面。目睹了百姓被新法所害,他决定实行亲民政策,以仁抚民,转化民风。
马不停蹄地深入基层调研,田间地头、深山老林,与百姓席地而坐,嘘寒问暖,他的足迹遍及县治的角角落落。罗霄山脉下的雕陂村,乃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,山多田少,村民多以烧炭为生。他着布衣、踏草鞋,仅带两名衙役,蹚水爬坡,翻山越岭来到村子里。寺庙里的老僧,先是一怔,后激动地拉过他的手说道,“我活了八十多岁,从没有县令来过这里”。
通过日夜兼程的考察,他发现了危害百姓生存,也是造成官民关系紧张的一个紧要问题:盐税。近年朝廷改革盐法,使他所在的吉州等各州在原有广盐基础上,又要加卖巨量淮盐。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,推销官盐原是他的岗位职责,但在大蒙笼村,眼看着百姓家徒四壁还被征敛盘剥的窘境,他止不住心酸沉痛。“穷乡有米无食盐,今日有盐无米食。但愿官清不爱钱,长养子孙听驱使”。在时人因盐税上书而被停职的前车之鉴下,他依然坚定地发出了自己的控诉。
诸县争先恐后,唯独他消极怠工,成了唯一一个站在盐策反面的知县。
上级斥他执行不力,百姓们却心安神泰,大街小巷争相传诵,泰和来了一位与民同忧乐的“黄青天”。
自唐以来,县衙署堂前均立有戒石,然戒石有名无实,上亦无文,或弃之乱石草丛,或查无此物。五代蜀主孟昶有《令箴》文,太宗皇帝摘录数句以戒群臣。他以此事为慎,令衙役从乱石中寻得此石,召集县衙各曹属官规诫:自仕宦以来,多有自愧之感,今取此数句,刻于戒石上,欲诸位以此自勉自励,不得扰民伤民。说完,令衙役取来笔墨纸砚,以正楷书戒石文四句:
尔俸尔禄,民脂民膏
下民易虐,上天难欺。
随后令工匠刻于石上,用朱砂描红,使之醒目,立于县衙门前。
四
晚晴夕照。处理完积压的公事,他走出县衙,信步登上阁楼。这些日子,闲暇之时,他最欢喜,也是来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,舞文弄墨、追忆、展望、谈笑、放空。
阁楼始建于唐代乾符元年,初为奉祀西方慈氏(即观音大士)之所,名“慈氏阁”。宋初太常博士沈遵任县令期间,因政通人和、百姓安居乐业,常登阁远眺,心旷神怡,遂易名“快阁”,自得之意也。回首任职以来,在乡间访贫问苦、在衙署循循善诱,一系列改革下来,民风逐步改善,吏治逐步规范,虽然不免得罪一些官僚,但总归县泰民安,他长舒一口气,倒也算快意。
无边落木萧萧,放眼望去,紫瑶山绵延起伏、层峦叠嶂,潮涨潮落,云来云去,天空辽远而广袤,几只鸥鹭正载着天空优雅地滑翔。天高地迥,觉宇宙之无穷,他静默地伫立着,无限情思在风中涤荡。那个曾经写下“青衫乌帽芦花鞭,送君直至明君前。若问旧时黄庭坚,谪在人间今八年。”的少年郎,而今已谪在人间37年了,接近不惑,还是那个自云间下凡的仙吗?当他回过神,将目光收近,却见一弯秋月映照澄江,毫发无损、月辉分明。
这画面长久保持在那里,像钉在地上的画框。一切都是相对的:看似运动的,河流、白鹭、落叶,年年只相似;看似静止的,这月色,却历经阴晴圆缺,书写着“岁月”二字的深意,这阁楼,却换了一批又一批登高客。闲云潭影日悠悠,物换星移几度秋。上句还是仿佛能静置到地老天荒的潭影,下句便是星辰的乾坤大挪移。万般无常,坚固的只是时间的流逝,只是时间的长河里,每一个人浪花的身份。
他的目光再次收回的时候,曾经的悲愤与忧郁,渐渐转为平淡与空濛。

巍巍快阁屹立千年 (俞健华 摄)
五
这也是师友苏轼到黄州的第三个年头。朗朗秋月下,先生正携一壶浊酒,登临赤壁、俯江长啸,只见一只孤鹤洁白羽衣,戛然长鸣,掠舟西去。是夜,白鹤化作道仙潜入先生梦中,翩跹而来,拱手作揖,曰,“我知之矣”。是先生的心事都被鹤仙所了然吗?
他与先生多年书信往来,惺惺相惜,先生更是常在席间当众吟诵他的诗作,称他为“超逸绝尘”“心轻外物而自重者”。“乌台诗案”爆发,先生进入人生的至暗时刻,一般人避之不及,他反而加倍敬重,依旧写信和诗,遥寄思念。不久,两个人前后脚,一个到了黄州,一个到了泰和。
还记得先生给他回的第一封信:我本放浪形骸之人,与你相识高兴得很,何必谦恭畏惧?彼时,他便在心里下定决心以弟子之礼,追随终生。世人称他们为“苏黄”,他们不仅性情相近,更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,一样的生而聪颖,一样的狂狷豁达,一样的诗书双绝,一样的颠沛流离。
知交半零落。心中那架古琴,因故人而绝,早已落满灰尘。和先生一样,他需要酒,需要无常中的沉醉;需要墨,需要沉醉之后的恒定。
此刻,秋月瑟瑟,于水波中散发银色清辉,好似它本就长于其中,或者说,它是天空的遗珠,而江水是存放它的宝盒。它们都属低温系,一静一动,自成一体,自生韵律,将人领向时间之外。这一时期,他的诗依旧以杜甫的现实主义为宗,以道义为本,只是更注重谋篇布局,诗句更简洁,明晰磊落。11世纪江西诗派大放异彩,属于全国文坛的大事件,而他是开宗立派的祖师。谈及作诗的理论,他留下一幅白描:“无人知句法,秋月自澄江”。
他的书法同样“尚意”,意蕴的意、意境的意、意义的意。很难估量,在泰和数百次的登高给他的书法带来的是怎样的嬗变。眼前的江月,质朴清亮,彰显着自然造化的和谐与玄妙,他曾无数次地凝视,直到这景象凝进生命。拉康提出,“能指”总是在“所指”下面不断滑落,它们之间是断裂的,极不稳定的。“能指”是取决于“自我”的一种表象符号,“所指”是客观的无法抵达的真实。早于拉康八百多年的他,却野心勃勃,用一幅幅狂草,做着一场场将这两者融合乃至重叠的实验。他的笔墨,法度严谨,却又突破常规体例,随心所欲,收放自如,有一种前无古人的沉着痛快。“随人作计终后人,自成一家始逼真”,他追求的,正是一份真,不断逼近“所指”内质的真。
这一年,他日夜记挂的苏轼先生,于千里之外的萧索之地,以同样的目光凝视,凝视黑暗、凝视无常,东坡躬耕、雪堂弄墨,写下了《定风波》、《赤壁赋》、《黄州寒食帖》等诗书,度过了人生中至为艰辛,也至为光辉的岁月。
六
升华,是他们回以这段逆行的答案。而这份答案,还要追溯到他们参玄问道的热情。
他自小受佛道熏陶,故乡分宁禅门鼎盛,祖母和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,叔父精于相术,是他心中的漆园。到泰和后,偶有空闲,他便寄情山水佛禅之间。离泰和不远有青原山,山中有净居寺,乃七祖行思的修行地。他与高士周寿同游,共猿鹤一日雅;吉水大东山有南冈寺,他留此小住,与住持切磋义理。永和清都观的逍遥堂,他应邀前往参加下元节活动,写下“心游魏阙鱼千里,梦觉邯郸黍一炊”。
时代风雨飘摇,人生羁绊种种,禅宗讲求的是:向内关照,破迷开悟。紧要的,是如何安置这颗心的问题。入世与出世,儒释道,不断在他体内融合,发生着无声的化学反应。前者,把他定在当下,济世医国;后者,带他飞至虚空,遗世独立。
他再次抬起头,望向远处的赣江,渔火点点,三五艘小船以笃定的节奏,缓缓于江面滑移,鸥鸟将翅羽无限伸展开来,在夜空中划出洁白的弧线。他想象着自己也生出一对翅羽,飞上小船,笛声清袅,驶入无边浩渺,像墨游弋于纸。曷不委心任去留?他转身,端坐于案几前,持笔,挥毫写下这首《登快阁》:
痴儿了却公家事,快阁东西倚晚晴。
落木千山天远大,澄江一道月分明。
朱弦已为佳人绝,青眼聊因美酒横。
万里归船弄长笛,此心吾与白鸥盟。
也是这个秋,东坡夜饮醒复醉,三更归来,倚杖听江声,写下《临江仙﹒夜归临皋》,“长恨此身非我有,何时忘却营营。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”。在相同的夜色中,他们竟不谋而合,一个与鹤对话,一个与鸥结盟,客居异乡,却殊途同归,归于一叶扁舟,万里江海,随波流逝,任意西东。
七
此时的他不知道,这首诗将会成为他的代表作,快阁也因诗而传,名满天下,达官名流、饱学之士、黄冠草履纷至沓来,在江风的漫卷中留下诗句,不断加深着这座阁楼的内蕴。
登高,在泰和成为一种行为艺术。随着木阶的迂回升转,视角渐渐打开,心境也渐渐超脱,当站在最高层的廊台上时,只见江山广远,景物清华,水墨迤逦悠长。那是一个坚固的场域,它不再是一座阁楼本身,而是具备了更大的质量与密度,像一颗引力强健的星球。时空在这里发生扭曲,万物的运行速度慢了下来。
凉爽的七月,我们站在这里,我,泰和文友肖城生,还有原泰和县博物馆馆长肖用珩。肖馆长刚跟我们神采飞扬地讲完泰和“三奇”,其中一奇是黄庭坚认前世母,他的孝顺列入了中华二十四孝。和为官、为文、为艺一样,他的为人亦堪称千古典范。我们都不再讲话,肖主席依然撑着栏杆望向江面,我笔直站着,双手交叠于身后,与他望向同样的方向。
大风阵阵袭来,寂静中我感觉到时空漩涡般的扭曲,那些遥远的时间粘连了在一起,如同连贯的蒙太奇。先是滕王阁上意气风发吟诵“君子见机,达人知命”的王勃,然后是郁孤台上满含愁绪写下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”的辛弃疾,他们各自在赣江的上下游,与伫立中游的黄庭坚一脉相连,又遥相呼应。文天祥押往大都途中经过,念起父母邦,清泪不止;陆游登上高台,诗意压积成矿石,留下“诗境”笔墨;杨万里、周必大、杨士奇……窄束的木梯累积着越来越多的蛩音。接着,我看到了追风少年肖城生,依然是穿着干净的衬衫,双手撑着栏杆望向远方,眼睛和现在一样清澈空茫。他的母校,泰和中学,陆续有孩子被这高度所召唤,读书、打盹、出神,在扭曲的时空漩涡里与古人照面,也幻想着无限锦绣的未来。
八
这一座外观并不出奇的江南阁楼,在历史的长河里,遭遇洪水、战火、龙卷风,屡次被摧毁,又一次次坚定地拔地而起, 成为泰和县城鲜明而巍然的地标,也成为其源远文脉所在。
如今的快阁,是在龙卷风之后,国家拨款并泰和百姓捐资建成。新阁建在原来的台基上,比原阁高出近5米,琉璃碧瓦、雕龙绘凤,古朴且典雅,庄严而凝重。阁厅正墙嵌有黄庭坚像,右侧嵌石匾,为黄庭坚手书《戒石铭》(《戒石铭》在宋高宗的推动下,曾遍布全国各州县,成为官场箴规)。
黄庭坚曾谓弟子:“士生于世可以百为,唯不可俗”。弟子问,“何为不俗?”他回答,“临大节而不可夺,此不俗人也。” 他死后170年,被朝廷追谥为“文节”,正是因为感其节气与文品。离开泰和后,他又经历了贬谪德平、黔中、戎州等地,最后客死宜州。在翻云覆雨的命运中,他早已心如砥柱,得马失马心清凉,越是困顿苦难,这节气越如皎皎秋月映江天。
阁楼先于思想,思想却让阁楼历百劫而弥新。有一些精神,渐渐成为某种常数,正如颠扑不破的真理,那是先人经过千锤百炼给我们留下的思想模型。站在快阁的大风里,我感觉到了那隐秘而真切的信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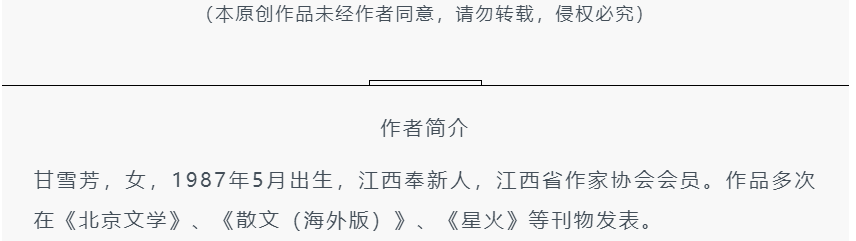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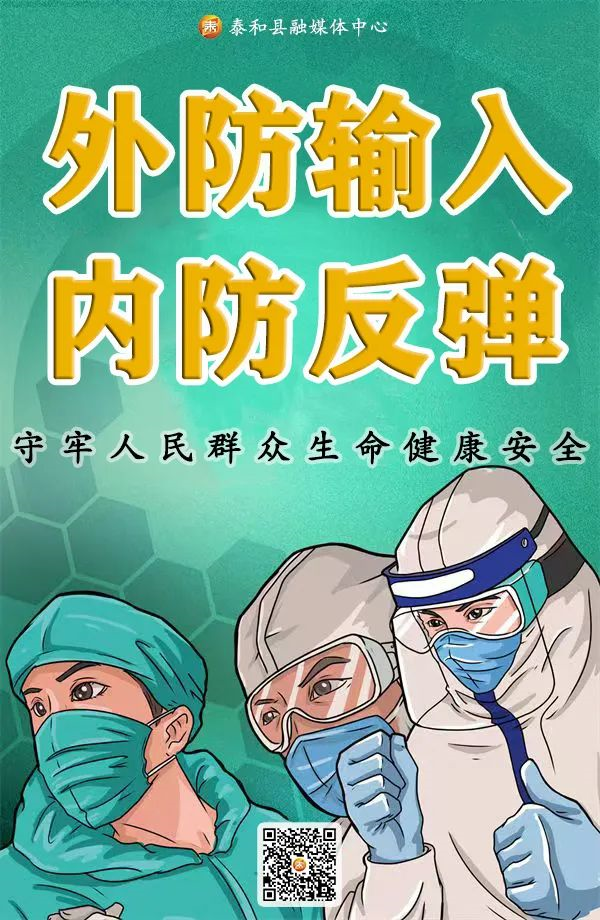
作者:甘雪芳
编辑:曹钦灵
编审:张静
监制:彭伟群




请输入验证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