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
谢谢您的关注,“泰和风”将陆续推出《主播带您听泰和》栏目,让泰和县融媒体中心的美女帅哥主播为身在天南地北的您,带来家乡最亲切美好的声音!
本期主播:张静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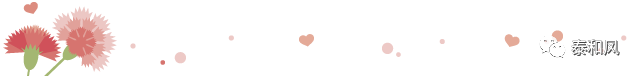

三千年前的沙村是什么样子,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,三千年前我们的先人曾在这里生活。 他们是千里迢迢赶来还是风尘仆仆路过?当他们和沙村山水相遇的时候,就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,他们开荒种地,捕鱼捉虾,然后生儿育女。这一片山水,是我们先人最初的家园。后来,有了文字记载“筑村沙溪,辟圩于沙洲之上”。原来,沙村是这么来的!



起初,沙村圩非常小,一条短短窄窄的青石板街,两排参参差差的木板房,后来改成砖瓦房,略为齐整了些,却依然是小。真可谓“一家酿酒,满街酒香;一家焙辣椒,全圩打喷嚏。”

直到现在,沙村也还是通往兴国的中心集镇,每逢当圩日,便人来人往,川流不息 ,连空气都陡然增加了热度。因为毗连的都是山区,原先交通不方便时,山民们春夏挑香菇、蜂蜜、杨梅,秋冬担生姜、竹笋、茶油来赶集,一担担挑来,一担担挑走,挑来的是一年的辛勤,挑走的是下年的期望。



每当夕阳西下,倦鸟归林,圩棚便飘来阵阵饭菜的清香。街道两旁一字儿摆开一桌桌丰盛的晚餐,沙村人家端着饭碗来来往往,你尝尝我的苦瓜鱼干,我品品你的红烧猪蹄,端起一碗米酒酿,醉红了云霞半边天 。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沙村人家派定了家的观念、根的观念,派定了与这块土地的深重缘分。
唐朝刘氏由金陵迁来,于沙溪建刘家村,县志都说“先有刘家村,后有沙村”。
高陇杨家的师鲁公从北宋而来,看见杨家村前珠陵江奔腾不息,村后彰法山万古长青便筑房屋,辟田地,种上稻和竹,平日荷锄扛犁,闲来读书吟诗,生生不息。
北宋景德年间尹居安(号缝源)于种地歇息时,看见一只母鸡北渡珠陵江,在河边芦苇丛中孵出一窝小鸡。认为此地为发族之地,遂拓基于此。可见,沙村人家尊崇的是自然万物。
百家姓百家长,沙村人家姓百家。沙村方言里,男孩唤着“细人子”,女孩叫做“娘子家”,黎明时分“天蒙蒙亮”,耕地叫“作田”,上学要喊“去书院”,说谎“打野哇”,丢脸叫“跌苦”。

最喜欢的是去乡村做客。 一进了村庄,你就听到狗吠声了,先是一只狗,继而是一群狗,此起彼伏的,叫的很响。汪汪的狗叫声中,主人斥喝着自家的狗,笑吟吟迎了上来。去沙村人家做客,你用不着扭扭捏捏讲客套,沙村人家待客热情得很,不顾你的再三阻拦,生火做饭。女人或到莲花塘捞尾草鱼,或到菜园里摘几把辣椒,或到床底下的瓦罐里摸几个土鸡蛋,瓜棚下的鸡群顿时炸了锅,一只肥肥的母鸡被罩住了……她不端盘子上桌,将大钵碗装满有瘦有肥的熏肉,客人用筷子夹一块,半个巴掌那么大,咬一口,满嘴油。她不用小酒盅待客,提一壶成年酒酿,满上一海碗,让自家男人陪客人开怀畅饮。她却站在桌边,大着嗓门对客人招呼:“恰,恰酒呀!冇有什么好菜,莫见怪……”话没说完就笑,笑出一脸的灿烂 。


从前,生活像蒿草一样的苦,沙村人家吹个唢呐苦中作乐,也要把日子过得亮堂堂。如今,更要把生活中的桩桩喜事和新事 ,谱成曲子和好节奏,磊磊落落,喜气洋洋地吹起来,敲起来,打起来。唢呐声长了翅膀,从沙村人家里扑楞楞地飞出来,掠过珠陵江,落在了泰和城里头 ,“沙村唢呐”成了泰和县出了名的民间技艺。

有曲就有歌,有歌就有戏,就有人拿起笔来写词写戏,就有人鸟鸣莺啭唱人生。从前,沙村圩的南街有个戏台,正对面的北街有个“万寿宫”,每年或隔年就有“木脑壳”的京剧班前来演出,连演十天半个月不消停,沙村人家听得是如痴又如醉。 “两步走来喂是喂,往前走来哟依嗨……”;“正月里,花里花朵开,花里花朵花里花朵一枝花……”。好一个《俏妹子》,乡土小调调,明快又爽朗, 年轻后生子系着垂膝的腰带,踏着轻快欢朗的步子,夸张的姿势极尽挑逗诙谐。太娘子(大姑娘)手掩绯颜娇羞闭月,时而与后生子背依着相致别脸,时而羞滴滴地应和着后生子的动作,这时候,台下的沙村人家也会猛吹唿哨,搅起一锅“热汤”哟!
还真是一锅好香的牛血汤!沙村人家爱喝牛血汤,也喜欢做牛血汤,氛围最好的是热气腾腾,人气鼎沸的圩棚。 沙村人家一心一意地挥动着锅铲上下煸炒,热火、热油、椒粒、蒜瓣、料酒侍候着,先把收拾干净的牛肚、百叶、牛肠一样一样的放进滚水里,逮好火候,手托着牛血豆腐,用刀划拉它两三下,就跌进了热汤里,一翻一滚赶紧上碗,美味就在刹那间诞生。不用大快朵颐,放进嘴里就是齿颊留香, 再把汤汤水水吞了下去,香鲜辛辣在肠肚中化开,又从毛孔中沁了出来,沙村人家连眉梢眼角都洋溢些慵慵懒懒。眼前熏黑的墙壁、土炉子烧旺的火、嘈杂的圩棚以及从油毡顶漏下的一米阳光,多么家常。是啊,过小日子用不着太聪明,也用不着太多的想法,该是如何就是如何!
汤喝了,酒也足了,曲吹了,戏也看了,沙村人家回顾以往,体味人生,审视起自己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一节节岁月。

“野哇”不能再打了,“细人子”要“上书院”哩。祖宗留下了家训“簸箕晒谷,教儿读书”。祠堂里悬挂着“兄弟进士”“学士第”的敕制横匾 ,祖宗的荣耀还要发扬光大 !打小 ,沙村人家就听老辈子的人讲过,双状元曾雅彦草鞋写“一本堂”的故事,也听过杨家士奇白衣入相,四朝元老的传奇,至于尹直三入内阁,蝉联大学士的故事更是耳熟能详。对于沙村人家来说,崇文重教就更是另一种魅力和意义了。
“黄豆结荚双打双,毛竽结子帮连帮;穷苦人民闹翻身,肩并肩来膀靠膀。活着就跟共产党。”这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歌谣,红军用石灰浆涂写在沙村人家的墙壁,也刻在了沙村人家的心里。峥嵘岁月 ,陈毅, 曾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导了沙村苏维埃政权的创立 。可以说, 激情燃烧的沙村人家用铁的臂膀扛起了“苏维埃政权”的巨匾,169名烈士用热血浇灌了共和国的自由之花。
时间无言,山转水流 ,日子说过就过去了。只是,抖落了岁月的灰尘,披上了时代的霓裳羽衣,沙村依旧繁华喧闹,而沙村人家的坡屋顶,炊烟已袅袅……(刘晓雪)





请输入验证码